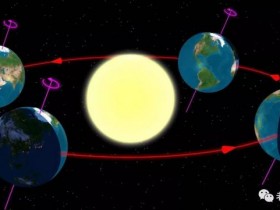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甘肃省宁夏府莲花池分州尚在陕西巡抚升允带领的新军的控制之下,兵灾连年,年号仍然因循大清宣统四年的年号。
当时升允正在攻打陕西“勤王”,连下十余城,一时间整个西北军派系林立,大战一触即发,好在升允知难而退,在陕西大儒牛兆濂的劝说下停止攻打西安,退兵甘肃一带驻防。饶忠厚的一个儿子饶良栋在西安求学,在战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饶忠厚看到饶良栋摘下帽子露出光秃秃的后脑,大吃一惊:“你的辫子哩!不人不鬼的,像个啥样子!”饶良栋笑道:“老爹诶!而今不流行发辫了,革命军拿下武昌,清朝皇帝退位,现时都改成民国了!”
饶忠厚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只知道改朝换代了,清家完蛋了。他将这个消息带到圆峁的时候,郝玉元惊奇地问:“新朝叫甚名儿?皇帝是谁?年号是啥?”饶忠厚一知半解道:“新朝叫民国,料是民朝,皇帝说是姓孙,年号也叫民国。今年算是民国元年。”郝玉元有些惊喜道:“改朝换代怕是要皇恩大赦哩。这几年的皇粮该能省下了。”饶忠厚咬着旱烟嘴道:“谁说不是哩?”这一年,果然没有了往日的皇粮和各种捐税。
民国二年,等到九、十月份荞麦收完,升允早已经到达蒙古争取外蒙古贵族王爷的支援,而花马池分州正式被民国军政府纳入治下,更名为盐池县,县府就设在原花马池分州衙门所在地。盐池县军政府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征收钱粮,不仅征收民国二年的粮款,连同民国元年没有征收的也一并要求民人缴纳。
郝玉元在交完粮食之后,仍然有七个小洋的募款没能交齐,官府给发布的募款令限拖欠的民人一月之内交齐,逾期不候!惠安堡已经有人聚集到县府组织抗粮抗捐,官方派兵镇压月余方才镇压下去。最终县府也作出让步:冬至之前必须足额缴纳,逾期以违抗军政府令论处。
郝玉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任何办法凑齐官家征收的七个银洋。如果此时到红井子把刚刚长起来的五十余只羊羔子卖掉,或许也能勉强凑齐,但是这是涸泽而渔的思维,以后再要置办这几十只羊就难上加难了。
郝玉元正发愁间,张广荣来串门了。见郝玉元满面愁容,张广荣却笑道:“岳丈你嫑熬煎,现时去惠安堡背盐的人多,你要是舍得下力气,只要不被抓住,背上两回盐就把钱粮赚回来了。现如今庆阳的盐价打滚地涨哩!”郝玉元想起曾经在莲花池晒盐的场景,心想这倒是个好办法,于是安顿了妻儿老小,翌日就赶着一头从张广荣家借来的瘦驴去惠安堡背盐去了。
从圆峁到惠安堡有百余里地。这样一头瘦驴,要想多驮盐,必须最大限度地节省驴的体力,郝玉元甚至不敢骑着,只能一路牵着毛驴走到惠安堡。
到了惠安堡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夜风吹在身上。阴冷瘆人,空气中一股干燥而咸咸的味道。郝玉元在距离盐场较远的地方拴了驴,驴不能拴得太近,被发现是要被没收的。趁着夜色,郝玉元拿出两个用羊皮缝制的大口袋,缓缓走向盐场——这个维系着他们全家生计的所在。
对于盐场郝玉元再熟悉不过了,他按照以往的经验,在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蹲守着。待巡视的看守从这里走过之后,郝玉元放心地笑了:“与莲花池盐场的巡视规矩都一样样的。”巡视的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郝玉元拿出口袋,轻轻地把这白色的晶体装进去。
两袋盐足足有二百斤重,他自然不会现在就把盐全部背走,因为只有一个人,也不能一袋一袋分开背。他把装好的盐袋埋进盐堆里,然后静静地等待一个绝佳的时机。等巡视的人员再一次经过这里时,他就知道,这两袋盐已经姓郝了。
依然是等待着脚步声渐渐远去,他才从容不迫地一次性背起二百斤的盐,举重若轻地朝着拴着毛驴的地方走去。
战争让整个西北地区的物资处于严重短缺的境地,油盐等基本的生活物品奇缺。食盐的官价由最初的一百文涨到三百文,民国元年涨到四百五十文,今年价格依然在上涨。而随着偷盐的人不断增多,私盐价格有所回落,但也要两三百文左右一斤。兵荒马乱的年月,只要有人能弄到这样的紧俏商品,就不愁赚不到银钱。
郝玉元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码算着这一趟买卖的实际收入:三百文一斤,也就是新币一角,二百斤就能换得二十个银洋,给官家七个,还余十三个。即便是二百文一斤,也合新币六分六厘,二百斤也能换得十三元。他心里想着,无论如何也够给官家的税金了。
他自然不敢停下脚步来,却也不敢走得太快,毕竟这头瘦驴驮着的二百多斤的食盐是关乎全家命运的最关键的物资。
毛驴突然停下来,让郝玉元心里一沉:莫不是遇到狼了?转身再看那驴,一身明晃晃的汗淌湿了毛皮。他明白了——这头瘦驴在走了一百多里的路之后早已经筋疲力尽。他取下一袋盐背在自己身上,赶着毛驴继续朝着庆阳方向前进了。
一来一去五天的路程,郝玉元只用了三天,第四天一早上,在庆阳一个同乡家休息了一晚的郝玉元载着满满两袋子米面,一步不敢停歇地赶回去了。
郝玉元不仅换来了两袋细粮,还获得了二十三个银洋,除去交给官家的七个,自家手里就还有十几个银洋的赚头,这可是能买三十只羊的钱啊!此次背盐下庆阳的另外一个收获是他独自一人扛起二百多斤盐还要走路赶驴,对此,人们纷纷竖起拇指,都顶佩服郝玉元是一条硬汉子。
谁料到这消息传到了盐场把总的耳朵里,他派人找到郝玉元:“你要是能把二百斤盐扛起走一里路,以后每个月送你二百斤盐!”郝玉元称自己从未去过盐场,哪里来的背盐之事?来人不信,郝玉元解释道:“当时只不过是用黄皮子换了百余斤米面,因赶着瘦驴,只能扛着粮食骑驴回来,不想村民们以讹传讹。”来人这才大笑不止离开,原本对于扛二百斤盐也并不甚相信,如今反成了笑话不断传扬。
生贵不解地问:“老爹,有这么好的事情为甚不去哩?”郝玉元严肃道:“为生计干下偷盐的营生,能扛千斤也不值得宣扬。如今主家找上门来,明里是看稀罕,暗里是给咱披贼皮!更是把咱当猴耍!记住,以后这类事情不能再干!”
郝玉元将毛驴送到张广荣手里的时候,张广荣看着喘息不止的驴笑道:“我这驴为老泰山这一趟立下了汗驴功劳!”说完赶紧就把郝玉元让进窑里。张广荣原本看着老实巴交,如今混得熟了,爱耍笑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原来,张广荣在当地有个绰号叫做“张捣鬼”,最喜偷奸耍滑,开人玩笑,甚至捉弄人,往往一句玩笑或者一个恶作剧弄得人哭笑不得。
张捣鬼曾经在一条官道旁的榆树上挂一条黄鼠,又在下方的土地上摞上石块,其中一个石块稍稍用木棍顶着,石块前面是一个陷阱大坑,坑用树枝苫上,里面全是牛粪,来人要取得黄鼠,就必然要站在石块上,石块很不稳当,人站上去之后就要要往前倒落,最终一脚踩入陷阱而踩一脚牛屎。他则躲在沟里看着贪心的人的狼狈相哈哈大笑。
正因为如此,人人见他纷纷躲避,以免着了他的道。他却乐此不疲,郝玉元曾经说过他:“你如今也成家了,有了家业的人嘞。咋能还这么嘻嘻哈哈地没个正型?以后好好过日月,不要一天不务正业。”张广荣嬉皮笑脸道:“记下了!”然后转身就又嬉闹去了,郝玉元看着这女婿的样子,摇着头不再言语了,只是心里隐隐觉得:妮儿嫁给这号爱耍的人,怕是要遭些罪。以后还要好好经管才行。
话分两头。郝玉元还清了粮款,又平安归来,圆峁上的这一家子沉浸在过节一般的喜悦中,郝玉元不顾口舌生疮、嘴唇干裂,从褡裢里面拿出了珍藏着的桂花糖,两个儿子一人一块,他吩咐生贵:“给你姐送一块去!”生富抗议:“咋不叫我送去?”魏氏笑道:“叫你送怕是送到半路就没有了。”正说话间,生富的一块桂花糖已经吃完,而生贵只吃了一半,他把剩下的一半糖塞到弟弟生富手里就出门了。
一百多只羊算不上多,但也绝不算少。郝玉元用女儿的婚姻换来的土地,获得了在盐池圆峁这块地方生根展叶的机会。
日子依然艰难地按照固有的模式过着,一家人总算平平安安,其乐融融。圆峁的这个人家彻底过期了半耕半牧的日子,郝玉元日月虽然艰难,却也还过得去,再未去过惠安堡盐场。
到了民国九年,郝玉元的女儿郝氏和张广荣终于完婚。眼瞅着郝生贵的年纪越来越大,郝玉元心里又着急起来。郝生贵已经十七岁了,虽然老实肯干,却总是喜欢跟一群娃娃家到处浪荡,耍钱摇骰子。这个年纪必须有个人拴住他,要不然他浪圆了,就收不住心了。嫁出去一个女儿,魏氏又是一个不太精明的妻子,这个家里急切地需要一个能干的婆姨。俗话说得好:“男人是耙耙,女人是匣匣,不怕耙耙没齿,就怕匣匣没底。”郝玉元利用在西梁、西湾、圆峁甚至罗渠和红井子认识的有限的熟人,不断地游说,让人家给郝生贵踅摸一个好人家的闺女。
说媒的事情很快有了眉目,有人把齐新庄的齐氏说给了郝家,郝玉元亲自去看过一回:齐家为人正派,家教严格,齐氏也落落大方,精明能干,只是身体有些单薄。于是,郝玉元就暗暗许下这门婚事。
齐家也知道郝家一个外来客户,能够在人生地不熟的盐池落脚,必然是顶勤谨忠厚的人家。加上郝玉元改造解地的犁铧、独自一人背盐下庆阳的轶事早已经在当地广为流传,于是也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即便郝家如今家业尚小。
亲事很快这么定下来了,郝玉元家底太薄,很多人担心郝家能不能拿得起“抬礼”。郝玉元卖粮卖羊,把辛苦积攒下来的银钱和布帛全部拿出来,凑了一份大礼给齐家送了过去,双方都很满意。众人纷纷称赞郝家仁义。
郝生贵在匆忙而不知所措中成家立业了。婚后他更加成熟和勤谨,更加舍得出力气。郝家在圆峁的日子过得安稳而平和。
结婚不久,齐氏怀了娃娃,不久却告流产。年长的妇人得知,带着鸡蛋来看望齐氏,劝慰她道:“你还太小,身子单薄,不好坐胎,以后大一点就好了。”然而连续三次怀孕却都流产。这下子一家人都慌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咋办。齐氏更是每日以泪洗面,对于生贵亲手熬制的鸡汤看都不愿意看一眼,让身子更加虚弱。
村里年长的人对郝玉元道:“怕是有啥冲撞哩,你去定边红柳沟的让瞎婆子给看一下,开个方子。这么下去可弄不成。”郝生贵将将送走长者,就去张广荣家借驴,然后立即骑驴去了红柳沟。
一路上,郝生贵匆匆忙忙着急赶路,将天黑的时候,才在红柳沟城边的一孔烂窑口见到了坐在石头上抽旱烟的瞎婆子,这婆子一张煞白的脸,在一明一灭的烟火中泛出青白的光。
那婆子不等郝生贵说话,就问他:“哪一家的?”郝生贵喘着气道:“花马池圆峁郝家。”婆子点头道:“知道了。你现时牵驴朝回走,谁叫你都不答应。婆姨生产的时候宰杀一只羊,血光能冲灾祸。”郝生贵把备好的银洋放在婆子手里,转身就牵着驴回了。
一路上,郝生贵心情紧张,不敢回头,等回到圆峁都到了后半夜了。过了三个月,齐氏显露出临盆的迹象,一家人都高兴而担忧,高兴地是要迎接着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担忧的是怕又出现什么岔子。郝玉元提前就把一只活蹦乱跳的羊羔子准备好了,拴在了窑洞口的榆树上。
接生的是村里最德高望重而子嗣兴旺的儿女双全的全户婆姨,妹妹张郝氏在灶间烧水,魏氏被安排在厨房帮忙,郝玉元因为不太方便留在家里,牵了羊出去了,却又担心不敢走远,就在半坡上坐着,偏着头随时留心听着家里这边的声音。
窑洞里发出齐氏痛苦的呻吟声,郝生贵手里拿着刀随时准备对准这头羊羔,只听窑洞里一个婆姨大喊一声:“张宝杀羊!”郝生贵小名叫张宝,一听这话手持尖刀,准确地捅进了被绑在榆树上的小公青山羊的心脏,一片红光闪过,那羊惨叫一声就倒地不动了,窑洞里同时间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婆姨们满头大汗从窑洞里出来,满面倦容地道:“张宝当爹了。你女人给你生了个儿!”郝生贵不顾死在地上的羊,连刀子都没有来得及扔下就要跑进窑洞,却被从外面回到家里的弟弟郝生富一把拦住,抢了他的刀子扔到地上。
新生命在圆峁的降临,让一家人看到了生的希望。郝家在盐池的第三代人出生了!这是各新生命是一个家族繁衍的希望!
“这娃娃的命是羊的命换来的,小名就叫羊换儿吧。”齐氏点头称是。郝生贵彻底禁绝了年少时和周边后生们一起浪荡染下的坏毛病,耍钱是彻底不参与了,喝酒也经常寻不着人了,唯有抽烟成了他劳作之后唯一的享受。他把裁好的烟叶子卷起来塞到旱烟锅里,每天夜间,蹲在窑洞门口,听着羊换儿哭哩笑哩,心里别提多美气了。
等羊换儿过了百天,郝生贵好好地备了一份厚礼,专程去了一趟红柳沟找见了神婆子,恭恭敬敬地送上了这些礼品,那婆子一张冷脸,也不说高兴,也不说不高兴。只是冷冷地点一点头,算是招呼了。
不几年,齐氏又生了一个儿子,母子平安,一家人其乐融融,郝玉元这才彻底放心了:郝家人要在这里扎根展叶了!当年从神木府谷逃难到莲花池,从一无所有,到添丁加口,两个孙子长得稀欠而健壮,人见人爱,在这个圆形的山峁上,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经过几年的经营,郝家在圆峁获得了三百余只羊,从女婿张广荣手里陆续获得的一百九十五晌地,此时在郝玉元和两个儿子的辛勤劳作下,也越发地获得了滋养,地不欺人,地里产出各种各样的粮食:荞麦、豆子、糜子、谷子……郝氏家族的先人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血汗,用他们的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家族繁衍生息的机会。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